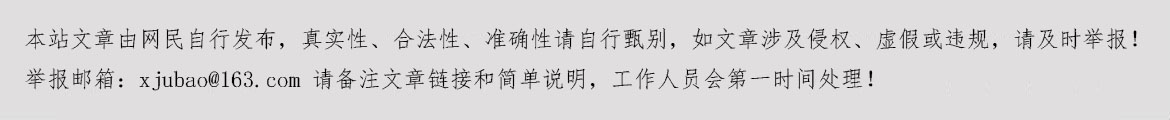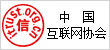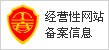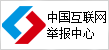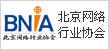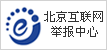名录网是领先的新闻资讯平台,汇集美食文化、商旅生涯、生活百科、教育科研、国际资讯、综艺娱乐、等多方面权威信息
风声|民营医疗机构合法融资、上市、营利,有什么错?
2022-03-18 10:39:19
作者|顾昕
遥想1992年,伟人邓小平叫停了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论,一度跌入意识形态陷阱的中国改革开放伟业,得以重新起步。正是由于市场力量的飞速壮大,30年后的今天,中国才得以在大国竞争引致饿狼环伺的险恶国际环境中巍然屹立。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内部依然存在着为数不少的意识形态游击队,常年在诸多社会经济领域挖坑、埋雷、放箭,为其通过话语生产获取一些蝇头小利而不懈努力。
这样的意识形态游击队,在中国医疗卫生健康领域常年存在。众所周知,自2005年始,游击队员们在有关新医改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争论中取得了不少胜利,俨然发展壮大;尽管国家新医改方案早已将促进民营医疗卫生健康服务机构的发展定为国策,国务院及其相关部委也颁发诸多文件推进所谓“社会资本”(即非政府公共财政投入)进入医疗卫生健康领域,但是意识形态话语流矢依然无所不在。
在2022年之春,正当中国政府、市场和社会在抗击新冠疫情的险恶战役中砥砺前行之际,意识形态流矢射向了中国健康产业中的营利性机构,迫使主管医疗卫生健康公共政策决策咨询的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向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所、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等组织发出公函,函请其协助提供能够回答以下三方面问题的研究资料:一是营利性医疗机构上市融资是否符合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二是营利性医疗机构上市融资是否会在医疗行业内产生不良示范效应;三是营利性医疗机构上市融资是否会导致社会资本在医疗领域无序扩张风险。
据媒体披露的公函内容显示,负责决策咨询的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此次调研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办医持续规范发展”。如前所述,自2009年新医改大政方针确立以来,国家促进健康产业健康发展的终极政策目标,始终没有改变。早已载入健康中国战略的政策,也不可能中流矢而亡。社会办医还是要发展,健康产业毕竟还是产业。但是,这样的流矢足以在一向杯弓蛇影的资本市场上引发一波海啸,撼动一片信心,造成一轮伤害。
流矢的指向:上市,还是营利?
令中国医疗卫生健康决策咨询部门感到需要调研的三个问题,箭头所向是营利性医疗机构是否应该上市融资。之所以是流矢,而不是实打实的进攻性武器,就在于其试探性。实际上,这些问题基本是伪问题,属于虚幻的靶子,而流矢的特征就是漫无指向。乱箭真正的标靶,并非上市的营利性医疗机构,而是所有营利性医疗机构。
道理显而易见。对于任何营利性机构来说,上市与否,只不过是其公司融资的一种手段,也是公司发展的一种手段。当然,只要不是很傻很天真,所有人都会明白,如果运作良好,公司上市会给上市前的投资人带来回报。上市后如果发展良好,公司会给新投资者带来回报。
因此,对于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关注的三个问题,很容易理出头绪。
首先,对于任何产业来说,允许其中的公司上市能否在短期、中期或长期一定促进该产业发展?
难说。毕竟在任何时期内任何产业发展与否,影响因素太多。但无论如何,一般认为,融资便利度或融资低成本是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这一点,对于健康产业来说,绝不可能有例外。基于常识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加以思维一定会得出如下判断:允许营利性医疗机构上市融资是否能促进健康产业发展犹未可知,但不允许营利性医疗机构上市融资一定不符合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
其次,公司上市融资会不会给公司所处产业带来不良示范?这个问题从何谈起呢?
显然,很多人看到公司上市后其原始股东持有者获利惊人,很容易联想或转化出这些公司上市带来“不良示范”的疑问。然而,这种“眼红效应”或“不良示范”的根源,往往不在于公司上市本身,而在于某种特定思维惯性的偏差。
这种思维惯性偏差,就是“幸存者偏差”,无论在精英还是普罗当中都普遍存在。
人们看到的自然是那些在惨烈竞争中优胜者得意之景,优胜者常被奉为“股神”,或者是资本运作“高手”,不一而足。至于“股神”或“高手”还在哪些其他公司持有原始股,而又有多少持股血本无归,他们自然不会“示范”,围观者也不会深而挖之。这一“幸存者偏差”思维的客观结果,自然无法为产业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眼亮效应”,从而产生风险意识健全的“心明示范”。
因此,营利性医疗机构上市融资是否会在医疗行业内产生不良示范效应这个问题,不需调研,答案很清楚:当然会。所有行业都有这个问题,或者说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痼疾。要治理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依赖于行政力量的干预,也不可能依赖于行政机制的运作,而是要致力于减少“幸存者偏差”思维的普遍盛行。在行政精英、市场精英和社会精英中减少这种有偏思维,并由他们向普罗大众示范这种偏差思维的偏差。在市场机制已经由党确定为基础性、决定性资源配置机制多年的中国,依然有漫漫长路要走。
最后,营利性医疗机构上市融资是否会导致社会资本在医疗领域无序扩张的风险?
基于常识和逻辑判断,这个风险自然有,而且不止在医疗领域,在所有领域都有。
因为资本市场中自然有投机性资本。没有投机性资本的资本市场根本不可能存在,投机性资本的运作当然也时常会给资本市场、金融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在当今世界可能从一地波及全球。对于这种风险的防范,是金融监管领域的巨大课题,也是棘手课题。笔者既非商学院教授也非金融学者,对此不予置评——这个领域中顶尖学术高手且自诩颇具社会责任感的精英是否给出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未可知。
具体到医疗卫生健康领域,这一风险自然是存在的,但有无必要视之为这一行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是大有商榷余地的。一来,“社会资本”并不见得充裕,无序扩张的可能性又有多大?二来,“社会资本”在医疗卫生健康产业中的投资者在风险控制上绝非白丁,他们不会对“无序扩张”的风险视而不见;三来,融资也好,投资也罢,非理性冲动难免。一时间的冲动会造成一时间的扩张,从投资冲动到理性投资总会一轮又一轮波浪性呈现,这是产业发展常态,健康产业绝不可能例外。无论行政、市场还是社会力量,试图阻遏一下惊涛巨浪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但试图压平这种曲线式波浪,不啻为异想天开。
综上,对于是否允许营利性医疗机构上市及其引发的问题,并不难判断。但是,相关问题的真正指向,仅仅是上市吗?事实上,在中国医疗卫生健康领域,始终存在着一种质疑营利性服务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其最为通俗的表达就是,既然为人民的健康服务是一种光荣神圣的事业,那么相关机构就不应该寻求赚钱。
这种话语与“全民免费医疗”的吁求搅拌在一起,更具有误导性。“全民免费医疗”,如果被正确理解为全民健康保险,在当今中国可以实行,而且应该实行,甚至是亟待实行,但其顺利前行必以扫清意识形态障碍为前提。对此,笔者将另文详述。这里,仅讨论一下营利性医疗机构在中国医疗服务体系中的定位。
营利性医疗机构到底应不应该得到发展?
这个问题本来不是问题,或者说是伪问题。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一个缕缕不绝萦绕于心的问题,同样在于另一个在国人当中普遍存在的思维偏差,即认定那些光荣神圣事业的从业人员就应该奉献。
君不见,教师被要求为“蜡烛”,在照亮别人的同时把自己烧干;医务人员被奉为“白衣天使”,既然是“天使”,自然不该拿高薪、住豪宅。更有甚者,义正辞严期望或要求别人“奉献”的人士,自己却极少“奉献”。事实上,有公立大学的教授,在倡导白衣天使或医疗机构奉献的同时,自己却享受着高额年薪以及不菲的非本职工作的创收。前述的“幸存者偏差”,那是一个国际性术语,因为那种有偏的思维,可谓人类现象,并非中国特色。但这里描述的期望甚至倡导他人奉献的思维,似乎颇具中国特色,如何命名呢?我姑且从善意视角视之,称之为“神圣感偏差”吧。
这种思维之所以有偏差,是因为枉顾常识且不计后果。
常识一,不论提供何种服务,或者说干什么事业,都有成本,其中包括人力成本,即从业者都需要赚钱。
常识二,从事何种行业不必强调光荣神圣,否则平等精神何谈。
常识三,诚然有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或知识密集型行业,但将某些行业视为奉献密集型行业,恐怕是无稽之谈。
常识四,无论什么行业的从业人员,都希望自己挣更多的钱,除非某些人已经挣到了无穷多的钱,才会宣称自己“不想挣钱”,但如此宣称的人如果不糊涂,也会说出如下精辟之言:“企业不赚钱是不道德的。”
常识五,如果某个行业平均而言赚钱少,或者其精英人士赚钱特别困难,那么这个行业大概率难以吸引青年才俊进入。
常识六,试图通过自己一技之长为他人提供更好服务的人士组织设立公司,是既有效率也更有可能有效果的行动方式。
医疗卫生健康产业的发展不可能背离这些常识。罔顾常识,对营利性医疗卫生健康服务机构无端质疑,或者有意建构某些话语,会产生一种反噬其身的后果。这就是营造出不利于医疗卫生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或舆论环境,让其中的从业人员无法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或者只能通过某些高风险行为才能收入不菲。其后果是,青年才俊进入医疗卫生健康行业的数量越来越少,高考状元们普遍不报考医学院,最终医疗卫生健康界人力资源后续乏力,“看病难”的问题呈现日趋深重之势,那些质疑者或话语建构者也难免自食其果。
事实上,自国家确立了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健康领域并大力发展健康产业的大政方针之后,有不少倡导医疗民营化的学者以及民营医疗机构投资者或从业者时常会有“春天来了”之语,但民营医疗机构生长的土壤仍相当贫瘠,其中营利性医疗机构顶多就是沙漠中的绿树,连绿洲都谈不上。
自2009年新医改正式启动以来,十多年过去了,民营医疗机构尽管在数量上早就大大超过了公立医疗机构,但在床位占比、卫生技术人员(医务人员)占比和收入占比上均未超过三成。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占比更微不足道,在医疗卫生健康产业中即便连补充性的定位都远未呈现。
对健康产业发展的土壤如不仔细分析并加以改良,而是关注沙漠中绿树带来的示范效应,从小处说,这是注意力资源的错配,从大处说,是对健康中国战略落地的干扰。
顾昕,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前新医改第七套方案(即北京师范大学方案)执笔人。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风声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本文作者立场。图源:视觉中国。转载事宜请联系风声君微信:formatkay
编辑|萧 轶